Nature:脑癌“星形母细胞瘤”起源之谜揭晓:致命融合基因,为何偏爱腹侧,还找到共同“命门”?
11小时前 生物探索 生物探索 发表于上海
《Nature》研究发现星形母细胞瘤中不同基因融合通过结合 “CGTT” 序列,靶向腹侧端脑神经前体细胞,激活 PDGFRA 通路致癌,OLIG2 抑制凋亡,靶向 PDGFRα 或成治疗新策略。
引言
大脑,这个掌控我们喜怒哀乐、思考决断的复杂器官,一旦遭遇恶意侵袭,后果往往令人心碎。在众多脑肿瘤类型中,有一种尤其棘手且令人困惑的存在——星形母细胞瘤 (Astroblastoma, ABM)。它虽然不那么常见,却以其高侵袭性、易复发性以及对年轻女性的“偏爱”而让医生和患者束手无策。更令人费解的是,不同ABM病例的肿瘤细胞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系列看似各不相关的基因融合 (gene fusions),如同大脑内部结成的多个“邪恶联盟”。
这些“错误拼接”的基因片段是如何让正常细胞癌变的?它们是各自为战,还是遵循某种共同的“行动纲领”?ABM究竟起源于大脑的哪个区域、哪种细胞类型?这些核心谜团长期笼罩在ABM研究的上空。
5月14日发表在《Nature》上的一项开创性研究“Oncogenic fusions converge on shared mechanisms in initiating astroblastoma”,终于撕开了ABM的神秘面纱。研究揭示:这些不同的ABM相关基因融合,尽管来源各异,却出人意料地“殊途同归”,它们识别并结合相同的DNA序列,进而惊人地特异性地改造了大脑中腹侧端脑的神经前体细胞 (ventral telencephalon neural progenitors)!
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不仅找到了ABM的精准细胞起源,揭示了不同融合基因协同致癌的关键分子机制,更令人振奋的是,他们还可能发现了这个“邪恶联盟”的共同“命门”,为未来ABM的诊断和靶向治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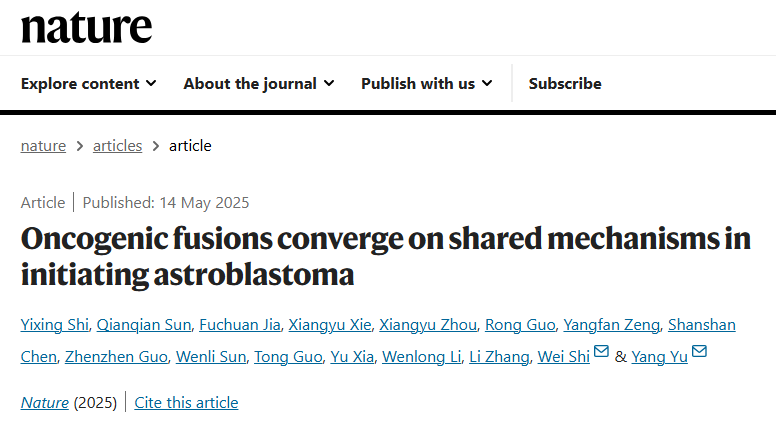
脑癌中的“身份谜团”:那些变异的基因融合
ABM最显著的基因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基因融合。研究人员发现,绝大多数ABM都涉及MN1基因的重排,最常见的两种是MN1-BEND2和MN1-CXXC5融合。当然,也有一些不涉及MN1的融合,比如EWSR1-BEND2、MAMLD1-BEND2或TCF3-BEND2。
想象一下,基因就像乐高积木。通常情况下,它们按照预设的方式组合和工作。但基因融合就像是两块原本不应该连在一起的积木强行拼接,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不稳定的结构——融合蛋白。这些融合蛋白往往会获得新的功能,或者以错误的方式行使功能。
那么问题来了,MN1-BEND2和MN1-CXXC5这些不同的融合,它们的“邪恶力量”来自哪里?它们各自为营,还是拥有共同的“行动纲领”?这项研究首先聚焦了融合蛋白中来自BEND2和CXXC5的这两部分,它们都包含预测的DNA结合域 (DNA-binding domains, DBDs)。
看似不同,实则“同道中人”:基因融合的秘密接口
尽管BEND2和CXXC5蛋白本身的序列差异巨大,但研究人员通过实验(比如SELEX技术,一种筛选蛋白与DNA结合序列的方法)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它们居然识别相同或非常相似的DNA序列!
具体来说,人源BEND2蛋白的BD2结构域(BEND2包含两个BEN结构域,BEN domains,命名来源于其保守的氨基酸序列)能够强有力地结合DNA上的“CGTT”序列。有意思的是,人源BD2中的一个关键碱性氨基酸R759对识别“CGTT”至关重要,而这个R759位点在BD1结构域或鼠源BEND2中并不保守,这暗示了CGTT结合可能与人源BD2的特定功能有关。
与此同时,MN1-CXXC5融合蛋白中的CXXC5部分,虽然结构与BEND2完全不同,但它所结合的DNA序列也包含了“CGTT”主题。通过晶体结构分析发现,CXXC5的CXXC结构域可以与含有“CGTT”的DNA形成复合物,并且主要通过与DNA中的C6、G7和T9碱基形成氢键进行互作。
这意味着什么?尽管这些融合蛋白的C端(来自BEND2或CXXC5的部分)源自完全不同的蛋白家族,但它们却通过结合同一个“CGTT”DNA序列找到了共同的“秘密接口”!这强烈暗示,这些看似不同的ABM相关融合,可能在下游的基因调控中殊途同归,共同驱动肿瘤的发生。
大脑的“爱恨情仇”:致命融合基因,为何偏爱腹侧?
接下来,研究人员构建了表达人源MN1-BEND2融合基因的小鼠模型,希望在活体中观察这种融合基因如何影响大脑发育。他们利用Cre-loxP系统,在胚胎发育第13.5天(E13.5)在小鼠的神经前体细胞中诱导表达MN1-BEND2。
结果令人震惊:MN1-BEND2在小鼠大脑的腹侧端脑 (ventral telencephalon),特别是内侧神经节隆起 (medial ganglionic eminence, MGE)区域,引起了显著的异常!与对照组小鼠相比,突变小鼠的MGE体积显著增大,平均体积增加了约41%。对MGE心室区(VZ)细胞的分析显示,增殖细胞(用KI67标记)的数量增加了约130%。这意味着MN1-BEND2极大地促进了腹侧神经前体细胞的过度增殖。这种过度增殖甚至持续到了小鼠出生后。
然而,在大脑的背侧端脑 (dorsal telencephalon),比如皮层区域,我们看到了完全相反的景象:细胞大量死亡!通过检测死亡细胞(TUNEL+细胞),研究人员发现在皮层的脑室/室下区、中间带和皮质板,死亡细胞数量显著增加。皮层厚度也因此变薄。进一步的实验证实,这种背侧区域的细胞死亡是由MN1-BEND2自主引起的。
这真是一出大脑的“爱恨情仇”!MN1-BEND2对于不同脑区神经前体细胞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它促进腹侧神经前体细胞增殖,却杀死背侧神经前体细胞。这一发现强烈提示,ABM可能特异性起源于腹侧端脑神经前体细胞。
生命守护者OLIG2:它如何让癌细胞“死里逃生”?
为什么腹侧神经前体细胞能够“扛住”MN1-BEND2带来的死亡威胁,反而开始异常增殖,而背侧的细胞却走向凋亡?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与一些能够抑制细胞凋亡的基因在不同脑区有差异表达有关。他们注意到,OLIG2这个基因在腹侧神经前体细胞中高表达,并且在人源MN1-BEND2+和MN1-CXXC5+ ABM中也富集表达。OLIG2已知在胶质瘤中抑制细胞凋亡。
为了验证OLIG2是否是腹侧神经前体细胞的“救命稻草”,研究人员构建了可以在表达MN1-BEND2的同时敲除Olig2基因的小鼠模型。结果证实了他们的猜想:在腹侧端脑神经前体细胞中同时表达MN1-BEND2并敲除Olig2基因后,MGE区域出现了显著的细胞死亡,TUNEL+细胞数量激增。这表明,OLIG2的表达对于腹侧端脑神经前体细胞逃避MN1-BEND2诱导的细胞死亡至关重要。
进一步在体外实验中,研究人员也观察到,在表达MN1-BEND2的皮层神经前体细胞中过表达OLIG2可以显著抑制细胞死亡。这进一步证实了OLIG2的保护作用。这提示,ABM细胞可能正是因为高表达OLIG2,才得以逃脱了原本可能触发的肿瘤抑制机制,走上了癌变之路。OLIG2就像癌细胞的“生命守护者”,默默抵御着死亡信号。
发育的“指挥官”失灵:细胞命运大乱,癌变信号亮起
MN1-BEND2融合蛋白是如何在腹侧神经前体细胞中“作乱”的?研究人员利用单细胞RNA测序 (scRNA-seq)技术,深入分析了小鼠腹侧端脑OLIG2+谱系细胞在表达MN1-BEND2后的转录组变化。
单细胞分析揭示了MN1-BEND2严重扰乱了腹侧神经前体细胞的正常发育和分化轨迹。与对照组相比,MN1-BEND2阳性细胞中,神经前体细胞样群体的比例显著增加(约占42.6%),而分化成熟的神经元(GABA能抑制性神经元)比例则大幅减少(从对照组的48.8%降至21.3%)。这意味着融合基因阻碍了细胞向正常神经元方向分化。
不仅如此,突变细胞在转录层面呈现出星形母细胞瘤特有的分子特征。研究人员定义了一组在人源MN1-BEND2+ ABM中特异富集的33个ABM核心特征基因。单细胞测序结果显示,在表达MN1-BEND2的神经前体细胞和胶质细胞中,这33个基因中有28个显著上调,与人源ABM肿瘤的转录特征高度一致。这证明MN1-BEND2成功地将细胞“转化”成了具有ABM分子特征的细胞。
形态学上,表达MN1-BEND2的细胞也出现了异常。它们会长出粗大扭曲的突起,并倾向于聚集在血管周围,形成了一种血管周占据模式 (perivascular occupancy pattern)。这种模式与ABM肿瘤中典型的星形母细胞假菊形团 (astroblastic pseudorosettes)高度相似,后者是癌细胞围绕血管排列形成的结构。这些现象都印证了融合基因对细胞命运和行为的深刻改变。
找到癌细胞的“命门”?靶向治疗的新曙光!
既然MN1-BEND2和MN1-CXXC5这些融合蛋白能够结合相似的DNA序列,并诱导共同的ABM特征基因上调,那么这些上调的基因中是否隐藏着肿瘤发生的关键驱动因素,或者潜在的治疗靶点呢?
通过对MN1-BEND2结合位点进行分析,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原癌基因 (proto-oncogenes)被直接靶向激活,包括PDGFRA、PDGFA和OLIG2。PDGFRA(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α)是一个已知的在多种癌症中异常激活的受体酪氨酸激酶,其下游通路(PDGFRα信号通路)在肿瘤增殖和存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MN1-BEND2阳性的小鼠细胞和人源ABM肿瘤中,PDGFRA及其配体PDGFA都显著高表达。
这一发现为ABM的治疗带来了新希望。研究人员在人诱导神经前体细胞(iNPCs,一种可以在体外模拟大脑早期发育的细胞模型)中表达MN1-BEND2或MN1-CXXC5。结果显示,这两种融合基因都能显著促进iNPCs的增殖,细胞数量大幅增加(例如,MN1-CXXC5导致细胞数量增加约63.6%)。当把这些融合基因表达的iNPCs移植到小鼠大脑中时,对照组iNPCs能正常分化,而融合基因表达的iNPCs却保持增殖状态,并形成了类似肿瘤的结构。
关键的治疗实验来了:研究人员使用了PDGFRα抑制剂Crenolanib和CP-673451,这两种药物已知能有效抑制PDGFRα活性。他们发现,用Crenolanib或CP-673451处理表达MN1-BEND2或MN1-CXXC5的iNPCs后,这些细胞的异常增殖被显著抑制。这直接证明了PDGFRα信号通路在ABM融合基因驱动的癌变中起着关键作用,并且靶向抑制PDGFRα可能成为治疗ABM的一种有效策略。
殊途同归的邪恶:解开星形母细胞瘤的奥秘
这项研究系统性地揭示了不同ABM相关基因融合如何“殊途同归”,驱动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它们通过结合共同的“CGTT” DNA序列,劫持了原本正常的基因调控网络,特别是直接激活了PDGFRA和OLIG2等关键原癌基因。
尤为重要的是,研究发现了肿瘤起源的细胞类型——腹侧端脑神经前体细胞。这些细胞因为特有的OLIG2表达而获得了对融合基因诱导的细胞死亡的抵抗力,进而被融合基因改写了命运,走向了过度增殖、分化障碍和获得ABM特有分子特征的癌变道路。
尽管不同的融合基因(MN1-BEND2 vs. MN1-CXXC5)有着不同的融合伙伴(BEND2 vs. CXXC5),但它们的核心DNA结合域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相同的“CGTT”序列,并通过激活共同的转录网络(包括PDGFRα通路)来实现其致癌目的。这种“功能趋同”的致癌模式,为ABM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ABM起源的细胞谜团,揭示了其核心的分子机制,还为ABM提供了新的靶向治疗方向。靶向PDGFRα信号通路,可能正是对抗这些“殊途同归”的致命融合基因的有效武器。虽然研究也提及了ABM在女性中高发可能与BEND2基因位于X染色体有关的有趣猜想,这或许是未来需要深入探索的方向。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就像打开了ABM这个“黑箱”,让我们看到了里面复杂的基因融合如何协同工作,精准打击大脑的特定细胞群体,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这些发现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诊断和治疗这种棘手的脑癌铺平了道路,为饱受ABM困扰的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Shi Y, Sun Q, Jia F, Xie X, Zhou X, Guo R, Zeng Y, Chen S, Guo Z, Sun W, Guo T, Xia Y, Li W, Zhang L, Shi W, Yu Y. Oncogenic fusions converge on shared mechanisms in initiating astroblastoma. Nature. 2025 May 14. doi: 10.1038/s41586-025-08981-5.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369078.
本网站所有内容来源注明为“梅斯医学”或“MedSci原创”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梅斯医学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为“梅斯医学”。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或“梅斯号”自媒体发布的文章,仅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站仅负责审核内容合规,其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不负责内容的准确性和版权。如果存在侵权、或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在此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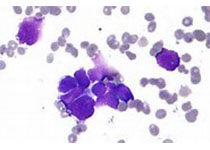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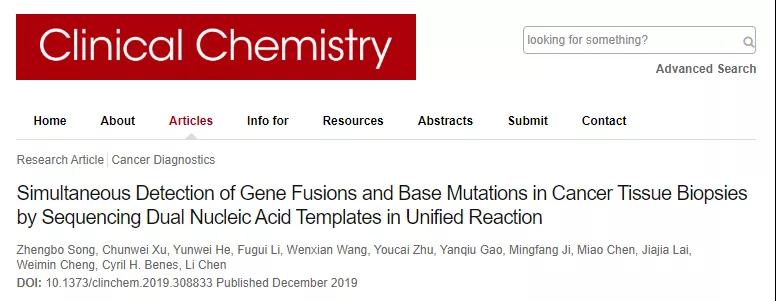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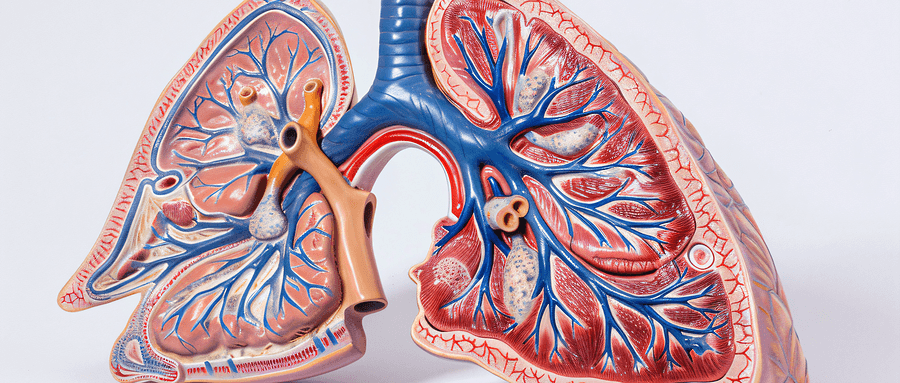





#基因融合# #星形母细胞瘤#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