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别只怪抗生素了!研究发现更多药物在影响你的肠道菌群
昨天 生物探索 生物探索 发表于上海
研究发现非抗生素药物可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组削弱定植抗性,增加肠道感染风险。地高辛通过激活宿主 RORγt 上调 BD-39,清除关键菌 SFB,抑制 Th17 免疫反应,该机制在人源化模型中保守。
引言
在我们与疾病斗争的漫长历史中,药物无疑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从一片小小的阿司匹林到复杂的靶向抗癌药,它们像忠诚的卫士,守护着我们的健康。然而,你是否想过,当你吞下一颗并非抗生素的普通药物时,你的身体内部——特别是那个被誉为“第二基因组”的肠道微生物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怎样的风暴?
我们的肠道中栖居着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被称为肠道微生物组 (gut microbiome)。它们不仅仅是“路人甲”,更是我们健康的亲密伙伴,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合成维生素、训练免疫系统,甚至还能抵御外来病原体的入侵。这种防御能力,被称为“定植抗性” (colonization resistance),是肠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然而,这道防线并非坚不可摧。
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抗生素会“无差别攻击”,在杀死有害菌的同时,也重创了我们的肠道菌群,导致腹泻等副作用。但一个日益引人关注的问题是:那些看似与肠道感染毫无关系的药物——比如治疗心脏病、高血压或精神疾病的药物——它们是否也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的微生物伙伴,甚至为病原体打开方便之门?
为了回答这个关乎亿万人用药安全的问题,研究团队展开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他们巧妙地结合了两种强大的研究手段:一是涉及超过一百万人的大规模流行病学数据分析,二是在小鼠模型中进行的严谨实验验证。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Nature》 上,“Identification of medication–microbiome interactions that affect gut infection”,该研究就像一部精彩的侦探小说,带领我们从海量的人群数据中寻找线索,在实验室里对“嫌疑药物”逐一“审问”,最终锁定“元凶”,并层层揭开其复杂的“作案手法”。

大海捞针:在百万人的数据海洋中撒下天罗地地网
想象一下,要从成千上万种药物中,找出可能增加肠道感染风险的那几个,难度堪比大海捞针。传统的临床试验耗时耗力,无法同时检测如此多的药物。为此,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极其巧妙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案例交叉研究 (case-crossover study)。
这种设计的精髓在于“自己和自己比”。研究人员并没有将服药的人生病概率与未服药的人生病概率进行比较,因为这两组人可能在年龄、生活习惯、基础疾病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会干扰结果。相反,他们关注的是每一个确诊为肠道感染的患者。他们将患者感染前约60天内(比如3-60天)的用药情况作为“案例期”,再将此人更早一段时间(比如63-120天)的用药情况作为“对照期”。
通过比较同一个体在“案例期”和“对照期”的用药差异,就能有效地排除掉那些长期不变的个体因素,如遗传背景、慢性病史、饮食偏好等。如果一种药物在“案例期”出现的频率显著高于“对照期”,就说明使用这种药物与近期发生肠道感染之间可能存在关联。
研究团队分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其中包含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地区超过一百万居民长达15年的医疗记录。这些记录详尽地涵盖了每一次的医生就诊、住院信息和处方药配药历史。这片数据的海洋,正是他们撒网捕鱼的绝佳场所。
初步分析结果首先给研究人员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发现,一些已知的“老牌嫌疑犯”,如抗生素 (antibacterials)、免疫抑制剂 (immunosuppressants) 和止泻药 (antidiarrhoeals),确实与肠道感染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例如,使用抗生素后,发生肠道感染的几率比 (odds ratio, OR) 约为 1.59,这意味着风险增加了约59%。这一结果证明,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可靠且有效的。
然而,真正的惊喜还在后面。在排除了这些已知的风险因素后,研究人员发现了一长串非抗生素类药物也赫然在列。这些药物来自不同的治疗领域,包括心脏病药物、降压药、抗抑郁药等等。经过严格的筛选(要求配药次数大于100次,几率比大于1.5,且统计学显著性P值小于0.05),他们最终锁定了21种“重点嫌疑药物”进入下一轮的调查。
在这份名单中,一个名字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地高辛 (digoxin)。这是一种古老的心脏病药物,用于治疗心力衰竭和房颤。数据显示,使用地高辛与肠道感染风险增加的关联性几率比为1.67,这意味着风险增加了67%。一个看似与肠道风马牛不相及的心脏药,为何会成为增加肠道感染风险的“帮凶”?这个巨大的问号,驱动着研究人员向更深的层次探索。
从大数据到小鼠:“嫌疑药物”的“庭审”现场
流行病学研究只能揭示“关联性”,而不能证明“因果性”。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使用地高辛的人更容易得肠道感染,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地高辛“导致”了感染。也许是那些服用心脏病药物的患者本身就体弱,更容易被感染呢?
于是,研究人员将战场从庞杂的人类数据转移到了严谨的动物模型——小鼠身上。他们将那21种“嫌疑药物”分别喂给不同组别的健康小鼠,然后用一种经典的肠道病原体——鼠伤寒沙门氏菌 (Salmonella Typhimurium, S. Tm) 来攻击它们。
为了更精确地研究肠道防线的“定植抗性”,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经过改造的、毒力减弱的沙门氏菌菌株 (S. Tm ΔinvA)。这种菌株无法有效入侵肠道细胞引发剧烈炎症,因此,它在肠道内的生存和繁殖数量,能更直接地反映出小鼠肠道微生物防线的强弱。如果一种药物破坏了这道防线,那么即便面对的是“减配版”的敌人,沙门氏菌的数量也会显著增加。
实验结果清晰地将“嫌疑犯”分成了几类:首先,研究人员检测了药物对小鼠肠道菌群结构的影响。他们通过分析粪便中微生物的β-多样性 (beta diversity) 来评估菌群的变化程度。这个指标可以理解为衡量两组微生物群落“有多么不同”的尺子。结果显示,多种药物确实显著改变了小鼠的肠道菌群构成,其中地高辛 (digoxin) 和多奈哌齐 (donepezil)(一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造成的影响尤为突出。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感染实验。在21种药物中,有4种药物在喂食后,显著加重了沙门氏菌的感染。这些药物分别是:地高辛 (digoxin)、氯硝西泮 (clonazepam)(一种抗癫痫和镇静药)、泮托拉唑 (pantoprazole)(一种抑制胃酸的质子泵抑制剂)和喹硫平 (quetiapine)(一种抗精神病药)。在这些药物的作用下,小鼠肠道内的沙门氏菌数量比对照组高出许多。特别是地高辛组,其病原体负荷的增加在统计学上极为显著 (P = 0.004)。
有趣的是,这些药物本身并没有广谱的抗菌活性。当研究人员将它们与从人体肠道中分离出的代表性细菌在培养皿中一起培养时,并未观察到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这说明,这些药物并非直接杀死了肠道细菌,而是通过某种更间接、更巧妙的方式,破坏了微生物组的平衡。
至此,流行病学数据和动物实验结果形成了完美的证据链。地高辛,这个最初的“重点嫌疑犯”,在实验室的“庭审”中被证实有罪。它确实能够独立地、显著地破坏肠道微生物的稳态,并削弱其抵御病原体入侵的能力。
地高辛专案:层层剥茧,解构“犯罪”现场
既然锁定了元凶地高辛,下一步就是要搞清楚它的“作案手法”。研究人员围绕地高辛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试图还原整个“犯罪过程”。
首先,他们确认了地高辛的“威力”。在独立重复的实验中,预先使用地高辛处理的小鼠,在感染减毒沙门氏菌12小时后,其粪便中的病原体数量比对照组高出约100倍 (P < 0.0001)!同时,它们的死亡率也显著升高 (P = 0.006)。
为了排除是病原体太弱的原因,研究人员换上了“完全体”的野生型沙门氏菌,并在一种对沙门氏菌抵抗力更强的小鼠品系 (Nramp1+/+) 中进行实验。结果依旧:地高辛依然能显著增加病原体负荷和致死率。这表明地高辛的破坏作用是普适且强大的,并非只针对特定情况。
那么,地高辛的破坏力是否只对沙门氏菌有效?研究人员又测试了另外两种不同的肠道病原体:一种是能引起小鼠结肠炎的啮齿类柠檬酸杆菌 (Citrobacter rodentium),另一种是医院内感染的“超级细菌”——耐万古霉素屎肠球菌 (VRE)。结果惊人地一致:地高辛预处理同样显著加重了这两种病原体的感染。
这一系列证据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地高辛的作用机制并非针对某一种特定的病原体,而是通过瓦解肠道菌群的“定植抗性”这一根本防线,从而为各种病原体的滋生创造了条件。这就像是城市的城墙被内鬼摧毁了,无论来犯的是步兵还是骑兵,都能长驱直入。
那么,这个“内鬼”究竟是谁?是药物直接作用于宿主,还是通过微生物组这个“中间人”?接下来,研究人员进行了两个经典的实验。
第一个实验:同居实验 (co-housing experiment)。
研究人员发现,并非所有品系的小鼠都对地高辛敏感。例如,常见的C57BL/6J品系小鼠在使用地高辛后,感染并不会加重。这是不是说明,地高辛的“魔力”需要特定的小鼠遗传背景或者……特定的微生物组?为了区分这两种可能,研究人员让本身不敏感的C57BL/6J小鼠与敏感的C57BL/6NTac小鼠在同一个笼子里“同居”两周。小鼠有食粪行为,这意味着在同居期间,它们会充分交换彼此的肠道微生物。两周后,研究人员将它们分开,再分别给予地高辛处理和沙门氏菌感染。奇迹发生了:那些原本“刀枪不入”的C57BL/6J小鼠,在获得了室友的微生物组后,也变得对地高辛极其敏感,感染后的死亡率显著上升!这个实验有力地证明,对地高辛的敏感性,是可以通过微生物“传染”的。
第二个实验:粪菌移植实验 (microbiome transplant experiment)。
如果说同居实验是强有力的旁证,那么粪菌移植就是决定性的“实锤”。研究人员将用过地高辛的供体小鼠的肠道内容物,移植到无菌(germ-free, GF)小鼠的肠道内。无菌小鼠的肠道里空空如也,像一张白纸,是验证微生物功能的完美模型。结果正如预期:那些接收了“地高辛处理后菌群”的无菌小鼠,在被沙门氏菌感染后,病原体数量急剧增加 (P = 0.046),死亡率也显著升高 (P = 0.005)。相比之下,接收了“普通菌群”的小鼠则安然无恙。
这个实验表明:地高辛对肠道感染易感性的影响,是完全可以通过微生物组来传递的。地高辛并不需要直接与宿主的免疫系统长期作用,它只需要扮演一个“点火者”的角色,引爆微生物组内部的变化,后续的连锁反应便会由微生物组自己完成。地高辛的“作案手法”,核心在于操纵了肠道微生物这个关键的“中间人”。
寻找“内鬼”:地高辛到底“收买”了谁?
既然确定了微生物组是核心案发现场,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地高辛究竟改变了微生物组中的哪个或哪些关键成员?
研究人员利用16S rRNA基因测序技术,对地高辛处理前后小鼠的肠道菌群进行了详细的“人口普查”。这项技术可以识别出菌群中的不同物种及其相对丰度。在纷繁复杂的数据中,一个物种的变化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在对地高辛敏感的C57BL/6NTac小鼠中,一种名为“萨氏候选菌” (‘Candidatus savagella’) 的细菌,在地高辛处理后几乎被“清零”了。而这种细菌,正是大名鼎鼎的分节丝状菌 (Segmented Filamentous Bacteria, SFB)。
SFB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肠道共生菌。它像铆钉一样,能紧紧地锚定在小肠末端的肠壁上皮细胞上。它的这种亲密接触,是向宿主免疫系统传递信号的关键。SFB被认为是肠道中最强大的Th17细胞 (T helper 17 cells) 诱导者之一。Th17细胞是免疫系统中的一类精锐部队,它能分泌白细胞介素-17 (IL-17) 和白细胞介素-22 (IL-22) 等多种细胞因子,像拉响警报一样,召集中性粒细胞等免疫细胞前来集结,并促使肠道上皮细胞产生抗菌肽,从而构筑起一道坚固的免疫防线。
可以说,SFB就像是肠道免疫系统的“金牌陪练”或“总教官”。有它在,免疫系统时刻保持着警惕和战斗力。而一旦失去了SFB,Th17细胞的活化水平就会大幅下降,整个肠道的免疫监控水平也会随之松懈。
研究数据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在地高辛处理后、SFB消失的小鼠肠道中,研究人员观察到,产生IL-17A的Th17细胞数量显著减少;作为免疫反应“步兵”的中性粒细胞 (neutrophils) 和作为“侦察兵”的单核细胞 (monocytes) 数量也大幅下降;与这些免疫细胞相关的基因,如Il17a、Il22,以及一些招募免疫细胞的关键趋化因子基因,表达量都显著下调。
至此,一幅清晰的犯罪逻辑图呈现在我们面前:
地高辛 → 导致SFB从肠道中消失 → Th17免疫反应被削弱 → 肠道免疫监控水平下降 → 沙门氏菌等病原体趁虚而入,大量繁殖。
地高辛通过精准地“狙杀”了肠道中的关键“哨兵”SFB,从而成功地让整个肠道防御体系陷入了瘫痪。
分子密语:地高辛的“作案手法”大揭秘
案件侦破到这里,似乎已经水落石出。但一个终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地高辛是如何杀死SFB的?它是一种专门针对SFB的“生物导弹”吗?
研究人员知道,地高辛在宿主体内有一个已知的靶点——一个名为RORγt的核受体。RORγt恰好是调控Th17细胞分化和功能的“主开关”。这个巧合让研究人员怀疑,地高辛可能并非直接攻击SFB,而是通过“劫持”宿主的RORγt,让宿主自己“动手”清除了SFB。
为了验证这个假说,他们利用了基因敲除小鼠。在缺乏RORγt基因 (Rorc-/-) 的小鼠中,地高辛的魔力完全消失了!即便给予地高辛,这些小鼠肠道内的SFB水平也安然无恙,感染沙门氏菌后也不会出现易感性增加的现象。
这个结果说明,RORγt是地高辛发挥作用的必要环节。地高辛的“作案路径”是:地高辛 → 宿主RORγt → 影响SFB。
那么,被地高辛“劫持”的RORγt,又是如何向SFB下达“死亡通知”的呢?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肠道上皮细胞产生的各种抗菌肽 (antimicrobial peptides, AMPs),这些是肠道天然的“抗生素”。他们通过RNA测序 (RNA-seq) 技术,系统性地分析了地高辛处理后,小鼠肠道中所有基因的表达变化。
在成千上万个基因中,一个基因的变化如鹤立鸡群,它就是 β-防御素39 (β-defensin 39, BD-39) 的编码基因——Defb39。数据显示,地高辛处理后,Defb39基因的表达量被急剧上调。而BD-39,正是一种抗菌蛋白。
现在,整个案件的分子机制终于被完整地拼凑了出来,其过程之曲折和巧妙,令人叹为观止:
- 药物劫持:口服的地高辛进入宿主肠道细胞。
- 信号转导:地高辛与细胞核内的RORγt蛋白结合,改变了其功能。
- 指令下达:被改变的RORγt启动了下游基因Defb39的转录程序。
- 武器生产:肠道上皮细胞响应指令,大量生产并分泌BD-39蛋白。
- 精准打击:BD-39这种抗菌肽,对SFB具有强大的杀伤力,而对沙门氏菌等其他一些细菌则效果不佳。
- 哨兵阵亡:SFB被宿主自身产生的BD-39大量清除。
- 防线崩溃:失去了SFB这个“总教官”,Th17免疫反应随之减弱,肠道免疫监控进入“休眠”状态。
- 敌人入侵:沙门氏菌等病原体发现防线洞开,便开始肆无忌惮地繁殖和扩散,最终导致严重的感染。
为了给这最后一环加上无可动摇的证据,研究人员还进行了两个关键实验:其一是体外杀菌实验,他们将纯化后的BD-39蛋白与从无菌小鼠肠道内容物中分离的SFB在体外一起孵育。结果显示,BD-39确实能直接杀死SFB,显著降低其活性。其二是转基因小鼠实验,他们构建了一种转基因小鼠,使其肠道持续过量表达BD-39。结果,这种小鼠肠道内的SFB水平天然就非常低,与被地高辛处理过的正常小鼠如出一辙。
这两个实验证明,BD-39是清除SFB的“充分且必要”的武器。地高辛的全部阴谋,就是通过RORγt,借宿主之手,生产出BD-39这把利刃,最终完成了对肠道关键共生菌的“谋杀”。
回归人体:这与我们有何相干?
故事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关键问题:SFB在小鼠肠道中很常见,但在人类肠道中却非常罕见。那么,这一整套基于SFB的复杂机制,对我们人类还有意义吗?这会不会只是一个“小鼠的特例”?
这个问题直击要害。如果该机制不适用于人类,那么这项研究的临床意义将大打折扣。研究人员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推断,尽管人类缺少SFB,但人类肠道中一定存在功能类似的其他细菌,它们同样扮演着刺激Th17免疫反应的“陪练”角色。地高辛的作用机制——通过抗菌肽重塑菌群、削弱免疫——这个基本逻辑应该是保守的。
为了验证这一点,他们再次请出了无菌小鼠,并给它们移植了人类的肠道微生物组。为了排除干扰,他们特意挑选了不含SFB,并且不含能够代谢分解地高辛的cgr2基因的健康人粪便菌群。这样一来,这些小鼠就成了拥有“人类肠道”的完美模型。
当这些“人源化”小鼠被给予地高辛处理后,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与之前在普通小鼠身上几乎完全相同的现象:小鼠肠道中,代表Th17免疫反应的关键基因,如Il22和Il17a的表达量显著下降;Defb39的表达量依然被上调;在用沙门氏菌感染后,地高辛处理组的病原体负荷显著高于对照组 (在回肠、盲肠、结肠和粪便中,P值均为0.008)。
这个实验的结果令人振奋。它有力地表明,地高辛通过重塑肠道菌群来削弱宿主免疫力、增加感染风险这一核心机制,在拥有人类微生物组的背景下同样存在!尽管发挥关键作用的“好细菌”可能不再是SFB,而是人类肠道中的其他成员(如某些梭菌或拟杆菌),但地高辛挑起的这场“内乱”的基本剧本,是跨物种保守的。
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药物安全?
从涉及百万人的流行病学警报,到一只小鼠肠道内单个分子的精密互动,这项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药物、微生物与宿主三方互动的壮丽画卷。它不仅仅是侦破了“地高辛”这一桩个案,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强有力的研究范式,去系统性地挖掘其他非抗生素药物潜在的微生物介导的副作用。
这项研究的意义是深远的:
首先,它提醒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药物安全。我们对药物副作用的理解,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药物对人体器官和代谢的直接影响上。这项工作揭示了一个巨大的“盲区”:药物对肠道微生物组的间接影响,同样可能是导致严重不良事件(如感染)的关键原因。未来,在评估一种新药的安全性时,或许需要将“微生物组毒性”作为一个常规的考量指标。
其次,它为理解个体化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什么同一种药物,对不同的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除了我们熟知的遗传差异,肠道微生物组的差异可能是一个同样重要的、甚至更易于改变的因素。就像实验中的两种小鼠品系,它们对地高辛的反应天差地别,而这种差别完全是由微生物组决定的。
最后,它为未来的个体化用药和精准医疗指明了方向。我们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当你需要长期服用某种药物时,医生可能不仅会考虑你的基因型,还会为你做一个肠道菌群检测。如果你的菌群构成显示你属于“高风险人群”(比如,你的肠道里富含能被药物清除的关键有益菌),医生可能会建议你更换药物,或者在使用药物的同时,补充特定的益生菌或益生元,来“保护”你的肠道防线,从而将副作用的风险降至最低。
这场由一颗小小的心脏药引发的肠道“血案”,最终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真相大白。但它所揭示的,不过是药物与我们体内亿万微生物伙伴之间复杂互动的冰山一角。在这片充满未知和机遇的领域,还有无数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探索。而每一次探索,都将加深我们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理解,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安全、更有效的用药时代。
参考文献
Kumar A, Sun R, Habib B, Deng T, Bencivenga-Barry NA, Palm NW, Ivanov II, Tamblyn R, Goodman AL. Identification of medication-microbiome interactions that affect gut infection. Nature. 2025 Jul 16. doi: 10.1038/s41586-025-09273-8.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670788.
本网站所有内容来源注明为“梅斯医学”或“MedSci原创”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梅斯医学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为“梅斯医学”。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或“梅斯号”自媒体发布的文章,仅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站仅负责审核内容合规,其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不负责内容的准确性和版权。如果存在侵权、或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在此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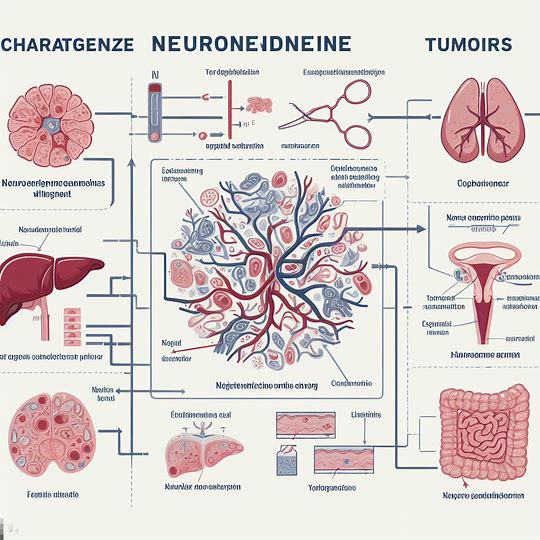









#肠道微生物组# #非抗生素药物#
7 举报